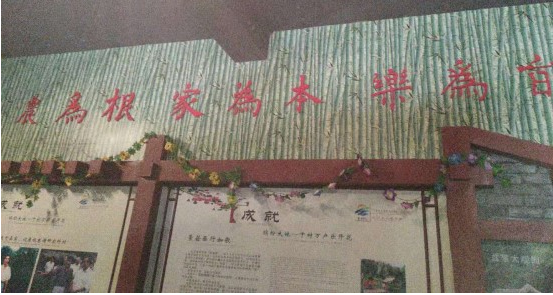1986年,在四川成都郫縣農(nóng)科村出現(xiàn)了國內(nèi)第一家“農(nóng)家樂”,時(shí)隔20年左右,在浙江湖州德清縣莫干山村出現(xiàn)了國內(nèi)第一家“洋家樂”(2007)。至今,兩個(gè)發(fā)源地都是國內(nèi)鄉(xiāng)村旅游的“示范區(qū)”,也都有著國家相關(guān)部門授予的“金字招牌”。作為一名關(guān)注鄉(xiāng)村產(chǎn)業(yè)發(fā)展的社科工作者,筆者將從社會(huì)學(xué)關(guān)于消費(fèi)層級(jí)、消費(fèi)群體、“消費(fèi)場所”、以及“地方消費(fèi)主義”等角度予以分析及闡釋。
“農(nóng)家樂”與“洋家樂”的發(fā)源地
農(nóng)科村,位于成都郫都區(qū)西北部(2017年郫縣并入成都市,稱作“郫都區(qū)”),作為曾經(jīng)的古蜀建都地,郫縣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。經(jīng)過30來年發(fā)展,農(nóng)科村陸續(xù)擁有了“中國農(nóng)家樂旅游發(fā)源地”(國家旅游局,2006)、“國家AAAA級(jí)旅游景區(qū)”(國家旅游局,2012)等官方授牌。按村工作人員介紹,農(nóng)科村現(xiàn)有30多戶農(nóng)家樂,規(guī)模大的有“徐家大院”和“劉氏莊園”,前者(含匯景園)占地80余畝,而“觀景樓”、“竹里灣”、“楊雞肉”等農(nóng)家樂占地約20-30畝。

農(nóng)科村“榮譽(yù)稱號(hào)”。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拍攝

農(nóng)科村徐家大院:“中國農(nóng)家樂第一家”
莫干山村(此處為籠統(tǒng)稱謂,因“洋家樂”同時(shí)存在于莫干山腳勞嶺、紫嶺、蘭樹坑等多個(gè)行政村),近年來以“洋家樂”而名聲大振,堪稱國內(nèi)民宿行業(yè)的“取經(jīng)地”。2016年,“洋家樂”成為國內(nèi)首個(gè)服務(wù)類生態(tài)原產(chǎn)地保護(hù)產(chǎn)品。其實(shí),早在民國時(shí)代,由黃膺白夫妻主持的“莫干鄉(xiāng)村改進(jìn)”,并不亞于晏陽初、梁漱溟等鄉(xiāng)建先賢的奉獻(xiàn)。
如今,以“洋家樂”為標(biāo)志的民宿產(chǎn)業(yè)不僅為莫干山村帶來了活力,也為整個(gè)莫干山鎮(zhèn)資源的盤活注入了動(dòng)力,是“鄉(xiāng)村引領(lǐng)小鎮(zhèn)”的一個(gè)典型例子,而莫干山鎮(zhèn)之所以能夠入選首批“國家級(jí)特色小鎮(zhèn)”(2016),“洋家樂”功不可沒。

“洋家樂”集聚區(qū)路標(biāo)
不同面向的消費(fèi)比較
如借用“川派盆景、川派琴藝”等講法,農(nóng)科村“農(nóng)家樂”消費(fèi)群體及其消費(fèi)形式的主要特征不妨概括為“川派式樣”的大眾旅游,關(guān)鍵詞有“大院莊園、奔放熱鬧”等豪放性語詞標(biāo)識(shí)。而莫干山村“洋家樂”消費(fèi)群體及其消費(fèi)形式或可概況為“海派式樣”的小眾旅游,關(guān)鍵詞有“精致悠雅、特立獨(dú)行”等婉約性語詞標(biāo)識(shí)。
作為鄉(xiāng)村旅游產(chǎn)業(yè)升級(jí)的一個(gè)新版本,莫干山村“洋家樂”對(duì)于長三角地區(qū)而言,特別為追求環(huán)保、自然等消費(fèi)時(shí)尚的“(準(zhǔn))精英型小眾市場”所青睞,以高端白領(lǐng)和外企人員為主要消費(fèi)對(duì)象,實(shí)際上,“洋家樂”最重要的客源就是來自于上海。
整體而言,除卻區(qū)位、在地文化和自然生態(tài)的差異性,無論是產(chǎn)品特色、經(jīng)營理念、客源市場,還是營銷模式等,“農(nóng)家樂”發(fā)源地與“洋家樂”發(fā)源地的鄉(xiāng)村旅游存在著較大差異。
例如,農(nóng)科村借助于西漢名儒揚(yáng)雄事跡之類歷史文化景點(diǎn),主要以盆景花卉進(jìn)行裝飾,餐飲、住宿、打牌(麻將)、喝茶等是當(dāng)?shù)?/span>“農(nóng)家樂”主要業(yè)態(tài)形式。大概在6、7年前,農(nóng)科村再度對(duì)基礎(chǔ)設(shè)施進(jìn)行了較大規(guī)模改造,包括“揚(yáng)雄廣場升級(jí)版”等景點(diǎn)的完善。原本樸實(shí)的“農(nóng)家樂”也陸續(xù)升級(jí)為星級(jí)鄉(xiāng)村酒店,但這種轉(zhuǎn)變屬于當(dāng)?shù)剞r(nóng)家樂的升級(jí)還是蛻變,尤有爭論。
比如,據(jù)村里介紹,歷經(jīng)30余年發(fā)展, “中國農(nóng)家樂第一家”——徐家大院也歷經(jīng)了4代變遷,第4代已轉(zhuǎn)型為四川省“五星級(jí)鄉(xiāng)村酒店”。然而,“請(qǐng)服務(wù)員打開房間查看了設(shè)施,發(fā)現(xiàn)是城市中二、三星酒店的設(shè)施,全無鄉(xiāng)村游的特色”。而且,2012年前后,在徐家大院實(shí)施第四代升級(jí)時(shí),村整體鄉(xiāng)村旅游出現(xiàn)了低迷趨勢,經(jīng)營戶之間分化加劇,不少是勉強(qiáng)維持經(jīng)營,經(jīng)營戶數(shù)量也從高峰期的過百戶減少到現(xiàn)有的30余戶(其中,核心景區(qū)的經(jīng)營戶從40多戶減少到10來戶),且客流量也不穩(wěn)定。
隨之而來的問題還有:大眾旅游取向的消費(fèi)群體,如何理解揚(yáng)雄事跡及其文化內(nèi)涵(比如,揚(yáng)雄與同樣活躍在郫縣的恩師、道家思想集大成者嚴(yán)君平的交往及其影響)?簡單復(fù)制靜態(tài)歷史文化景點(diǎn)是否能成功吸引“游客的凝視”?
然而,農(nóng)科村農(nóng)家樂發(fā)展到現(xiàn)在,好似越來越脫離了‘農(nóng)家’的本真,那么,什么才是農(nóng)家樂宜有的形態(tài)呢?擬定的“精品主題民宿集群”又將如何打造?
對(duì)此,村內(nèi)農(nóng)家樂史料館或許提供了一些詮釋。“戰(zhàn)后英國最重要的文化行動(dòng)主義者”雷蒙·威廉斯關(guān)于“鄉(xiāng)村與城市”的部分闡述也可提供參考:田園之樂、農(nóng)家之樂并非局限于“風(fēng)景如畫”,否則,將可能陷于“文學(xué)敘事”而漠視生活屬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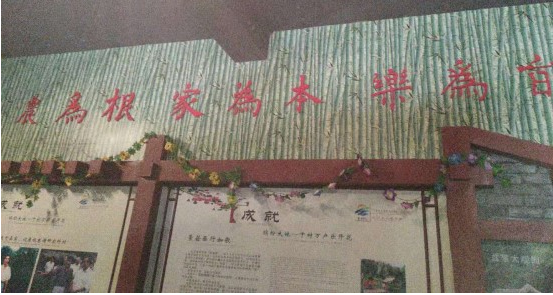
農(nóng)科村“中國農(nóng)家樂旅游發(fā)源地史料館”內(nèi)標(biāo)語
相較于農(nóng)科村農(nóng)家樂遭遇的發(fā)展困惑,莫干山麓以“洋家樂”為標(biāo)識(shí)的高端民宿已近百家,呈現(xiàn)出群落化發(fā)展態(tài)勢,個(gè)性化與多樣化同時(shí)并存。至于莫干山村“洋家樂”的休閑特色和消費(fèi)品格,筆者在2014年為地方政府部門撰寫的調(diào)研報(bào)告有過概括,即“土洋一體、新舊一家”,或稱之為“中西合壁、新舊同在”,這幾年持續(xù)觀察下來,依然覺得頗為恰當(dāng)。
“洋家樂”的成功,離不開自然田園和人文歷史等元素的融合,但關(guān)鍵在于旅游消費(fèi)需求轉(zhuǎn)型時(shí)期,實(shí)施了準(zhǔn)確的市場定位和營銷定位,比如,中高端消費(fèi)者對(duì)于“低碳環(huán)保、回歸鄉(xiāng)野”以及“伴城伴鄉(xiāng)、城鄉(xiāng)互動(dòng)”文旅消費(fèi)的渴慕,從而有助于“個(gè)性化消費(fèi)和社交圈子的形成”,關(guān)于這一特質(zhì),上海消費(fèi)群體尤為明顯。據(jù)上海籍調(diào)研者講述,如今在上海“成功人士圈子”,如還有不知道或沒去過莫干山“洋家樂”的,極可能被視為“落伍于時(shí)代的表現(xiàn)”。
然而,“洋家樂”發(fā)展存在的問題在于,受益于飛速崛起的集聚效應(yīng),近幾年,一些外來動(dòng)輒過千萬、乃至過億元的“大好高”項(xiàng)目陸續(xù)施工或建成,在促進(jìn)村鎮(zhèn)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和提升形象等“利好”訊息的背后,也需要關(guān)注生態(tài)資源的承載力以及反客為主式“縉紳化”對(duì)于山村造成的隱患。
無論是“農(nóng)家樂旅游發(fā)源地”,還是“洋家樂旅游發(fā)源地”,都只是招牌而不是品牌,品牌建設(shè)具有長期性和實(shí)踐性,而包括知名度、美譽(yù)度和忠誠度在內(nèi)的品牌塑造是一個(gè)系統(tǒng)工程。比如,官方授權(quán)的A級(jí)景區(qū)資質(zhì),并不意味著消費(fèi)者就會(huì)“買賬”(截至2017年底,中國共有4A級(jí)旅游景區(qū)3272 家);再比如,各式“特色小鎮(zhèn)”的建設(shè)也面臨著可持續(xù)性發(fā)展與利益相關(guān)者之間利益協(xié)調(diào)的壓力。
鄉(xiāng)村旅游如何適應(yīng)消費(fèi)升級(jí)
首先,觀光旅游及其之上的文化服務(wù)業(yè)之所以能成為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重要產(chǎn)業(yè),在于其服務(wù)于經(jīng)濟(jì)結(jié)構(gòu)的轉(zhuǎn)型與發(fā)展。依英國社會(huì)學(xué)名家約翰.厄里(John Urry)之見,“關(guān)于鄉(xiāng)村消費(fèi)的性質(zhì),需要置于鄉(xiāng)村消費(fèi)方式持續(xù)變化的情境之中加以探討”,于是,作為國內(nèi)鄉(xiāng)村游的特定呈現(xiàn)形式,“農(nóng)家樂”和“洋家樂”體現(xiàn)的是基于不同形式認(rèn)同的“消費(fèi)場所”(Consuming Places),可以看到,“人們逐漸將消費(fèi)場所重新建構(gòu)成消費(fèi)中心,成為商品和服務(wù)被比較、估價(jià)、購買與使用之脈絡(luò)”,就場所與消費(fèi)關(guān)系而言,“場所因?yàn)榫邆淠骋惶刭|(zhì)(文學(xué)、環(huán)境、工業(yè)、歷史、建筑物等),讓人們覺得它的地位重要,但這些特質(zhì)隨著長期之使用而漸漸枯竭、消失”。依據(jù)大衛(wèi)·哈維之見,為了吸引資本,不同的場所/地方也在竭力進(jìn)行各式各樣的自我營銷和推廣傳播。
其次,“地方消費(fèi)主義”是消費(fèi)社會(huì)學(xué)的一個(gè)術(shù)語,指的是隨著社會(huì)生產(chǎn)發(fā)展,消費(fèi)單位以及消費(fèi)者的消費(fèi)層級(jí)也在不斷擴(kuò)展,消費(fèi)對(duì)象范圍也在逐漸擴(kuò)大,例如,從對(duì)具體物品的消費(fèi)上升到對(duì)一個(gè)地方舒適物的整體性消費(fèi),或可稱之為“地方消費(fèi)主義”。
就此而言,“農(nóng)家樂”發(fā)源地與“洋家樂”發(fā)源地二者所居縣域也頗有可比性,例如,郫都區(qū)和德清縣均多次入選全國經(jīng)濟(jì)百強(qiáng)縣,前者從屬于成渝都市圈,距離成都市15公里左右;后者從屬于杭州灣都市圈,距離杭州市17公里左右。鄉(xiāng)村旅游和傳統(tǒng)農(nóng)業(yè)之外,兩個(gè)縣都在邁向生物醫(yī)藥等先進(jìn)制造業(yè)和部分先導(dǎo)產(chǎn)業(yè),只是前者側(cè)重于電子信息產(chǎn)業(yè),后者側(cè)重于地理信息產(chǎn)業(yè)。而且,郫都區(qū)和德清縣都以“國際化”為前進(jìn)目標(biāo),前者號(hào)稱打造“國際化都市新區(qū)”,后者則擬定建設(shè)“國際化山水田園城市”。
再次,對(duì)于鄉(xiāng)村旅游業(yè)發(fā)展而言,從“農(nóng)家樂”到“洋家樂”的轉(zhuǎn)變,不啻為一種消費(fèi)升級(jí)的體現(xiàn)。然而,在整體層面,鄉(xiāng)村旅游業(yè)“消費(fèi)升級(jí)”的實(shí)現(xiàn)程度,將受制于國家鄉(xiāng)村振興戰(zhàn)略以及“文化和旅游部”等調(diào)整后,政府機(jī)構(gòu)執(zhí)行力落實(shí)的實(shí)際效果。
至于郫都區(qū)和德清縣等地方性鄉(xiāng)村旅游場所競爭力的提升及其對(duì)消費(fèi)升級(jí)的適應(yīng),需要因地因時(shí)因商號(hào)而予以具體呈現(xiàn),需要關(guān)注消費(fèi)場所可賦予的意義及其差異特征的需求。其中,市場營銷、品牌推廣和審美需求(即消費(fèi)偏好的刺激與塑造)三者的聯(lián)動(dòng)推進(jìn)不可缺少,共同服務(wù)于差異化競爭,以助于“創(chuàng)制出個(gè)性化的與眾不同的賣點(diǎn)”。
為此,“技術(shù)升級(jí)和產(chǎn)品升級(jí)”之外,還需要以“服務(wù)升級(jí)”為導(dǎo)向,尋覓新的“細(xì)分市場”(利基市場/縫隙市場),當(dāng)然,這其中涉及諸多有待細(xì)化之處,比如經(jīng)驗(yàn)的積累、新興技術(shù)的理解和跟進(jìn),運(yùn)營流程的優(yōu)化和升級(jí),以及對(duì)消費(fèi)者消費(fèi)心理的深度思考和探究等,這都需要一步一個(gè)臺(tái)階,而不是一蹴而就。(來源:澎湃新聞)